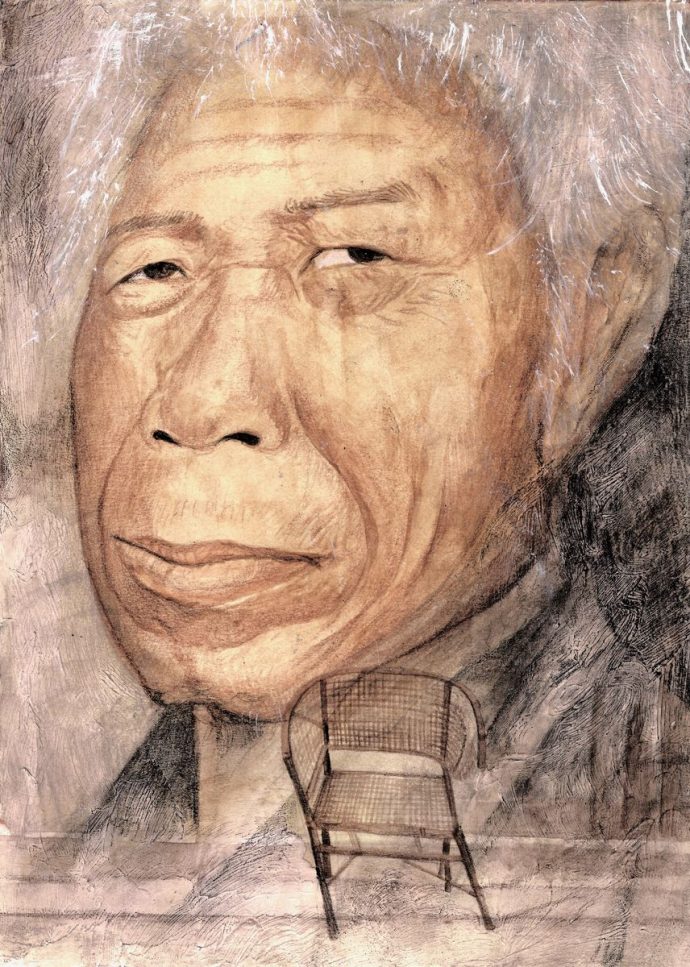離去的反倒是人。這是幢終年霉雨的屋子,地磚的顏色始終是哭過的,大片黃褐斑點羣聚天花板角落,狹窄的一字型廚房僅容一人,浴室的壓克力門板和塑膠浴缸皆泛成了舊牙的黃。搬家的過程是一場旋風,將我們連人帶傢俱刮進這間陌生的老屋裡。
⊙文/林巧棠(第36屆散文組首獎)
明明是回家,卻像是作客。
我端坐在曾經米白的沙發上漫不經心嚼著便當,一粒瑩白的飯粒掉在上頭,襯出它骯髒的灰黃。舉目四望,屋裡一切如舊,物件都好端端地待在應然之處:電視立在矮櫃上,茶几瑟縮屋角,沙發組圍著正方桌案擺放,一切仍是原先那個客廳的模樣。餐桌邊的餐椅仍是四張,就連需要清空才好搬動的冰箱──我不禁打從心底佩服起母親來──也不可思議的整齊,長據門側的醬油膏沙茶醬與沙拉醬等,瓶瓶罐罐依照高矮順序一字排開,彷彿它們自始至終未曾離去。
離去的反倒是人。這是幢終年霉雨的屋子,地磚的顏色始終是哭過的,大片黃褐斑點羣聚天花板角落,狹窄的一字型廚房僅容一人,浴室的壓克力門板和塑膠浴缸皆泛成了舊牙的黃。搬家的過程是一場旋風,將我們連人帶傢俱刮進這間陌生的老屋裡。
打從踏進大門開始,父親的叮嚀就未曾間斷:「電視遙控器換了」、「廁所燈在這裡」,但是他語句清淡,拖著將息未息的尾音,讓我誤以為自己僅是名即將遷入的房客,他不過是領我看屋的房東。
然而他為我做的卻遠比最好的房東多太多了。那些來不及開封的紙箱,一落落蹲踞在屋內各個畸零角落,大門邊,矮櫃兩旁,樓梯下方的凹壁,「裝有你東西的那幾箱,我全都用紅膠帶標好了」,他又指指我的舊電腦,自從買了筆電後幾乎沒再開機過,「電腦桌在這裡,桌上的東西我原封不動搬過來,印表機也裝好了」,他的語氣平緩如常,每次開口,卻只說一句就打住,頻頻回頭,彷彿在等待些什麼。
我究竟是怎樣一個冷漠的孩子,才能不回應他的所有邀功呢。
半小時前我踏出車站,家鄉烈烈的風以熟悉的力道撕扯我的長髮。即使大半視線皆被凌亂的瀏海遮蔽,我仍舊一眼便能從列隊的車陣中認出父親的那一輛。寬敞的車內,我卻被四面八方湧來的沉默壓得喘不過氣,幾乎窒息。父親總是率先打破靜默,說的都是意料之中的那幾句:
「錢還夠用嗎?」
『夠。』
「需要的話就直說。」
『謝謝。』
曾幾何時,我們的對話只剩下這些。
他以為畢業後我就要出國念書了。我說,打算就在國內念研究所。我沒說下去,他也沒問下去。突然他又提起股票盈虧之類的事,對那些運籌帷幄的名詞和策略,我是一點概念都沒有的,僅能回以幾個間斷的語助詞:喔。好。哇。
緊接著,一陣彼此最熟悉的沉默如海潮將我倆淹沒。這種沉默,自從他離開後我們練習過幾次,很快就上手了。我們不常見面,卻熟練得能夠立即築起一道緊實的隔音牆,讓所有的話語都在半空中碰壁,默契難得地好。
那些話或許是寬慰,意思是無論我想去哪裡念書,他都負擔得起。從後座斜斜往駕駛座看去只能看見父親的側臉,鬆弛垂皺的下頷,更加稀疏斑白的髮鬢……上回見面是過年,不是闔家團圓的除夕圍爐,而是大年初五。那時他的頭髮似乎沒這麼少。正午的陽光像針芒盡往眼裏扎,我幾乎不認識駕駛座上這個人了,就連不常見面的朋友也知道我將來的去向。
父親趁著年假出國了,和他的情人一起。
無論他給了多少關切,都會被年初五的記憶給強硬地取消──眼眶裡的水氣聚集成膜,酸苦的感覺像哽在喉頭的魚刺,吐不出也嚥不下。
他沒待多久就回去工作了,留我獨自在家,作客。手中的便當還是溫熱的,我非常餓卻只嚼了半個,再也吞不下。我將便當盒扔進塑膠袋內使勁綁死,等著傍晚的垃圾車。果皮菜梗,油漬屑渣,即使是最難處理的廚房垃圾,只要丟進袋裡交給清潔隊,自有專人打包所有煩憂,還我一幢爽然清潔的居所。我一面使勁打結一面想著,要是酸苦的記憶也能丟得如此乾淨就好了。
租來的房子很老,而且窄,上樓,下樓,不到三分鐘便逛完一圈。客廳裡還留著原屋主棄置的巨大電視櫃,深到發黑的原木色調令我想起奶奶家的那一座,集擺設與儲藏功能於一身,佔滿整面牆的龐大體積,再加上沙發組與大小几案,令原先就不大的客廳顯得更加擁擠。我走到牆邊,才發現角落裡還塞著一張單人沙發,兩邊各緊靠著一張長沙發,中間毫無可站之處,上頭胡亂堆疊著報紙雜誌與大賣場傳單,弟弟的舊背包被壓在最底層。
被棄置的單人沙發是爸以前常坐的位置。有一陣子他突然迷上看電影,不上班的時候,他會坐在那張沙發上,翹起腳,剝幾顆蒜味花生,手裡的遙控器總是在幾個洋片頻道切來換去,HBO、東森洋片、Star Movie,我們對這些好萊塢的片子已然爛熟於胸,熟到在頻道隨意切換後的五秒鐘內就能喊出片名和主要演員。從前他還在的時候,我們常打賭著玩,卻老是分不出勝負。
後來他嫌那些商業片總是一成不變,不看了,轉而前往百視達,每次都抱回一大疊片子,大多是歐洲或日本片。在家人都熟睡的深夜裡,他獨坐客廳,緩緩咀嚼花生,以及那些數分鐘內連一句對白都沒有的長鏡頭。有好一段日子,即使到了下午,DVD放映機的餘溫都還在。
不過,就在他把睡衣和牙刷都帶走,只留下那張就此冷卻的沙發之後,放映機就再沒有燒壞的可能了。
我上二樓打算整理衣物。主臥室裡有座高聳至房頂的舊衣櫃,櫃身是拙樸的深褐色,垂老的濃綠門板鑲著若有似無的黯淡金邊。這種脫妝的老傢俱除了放衣服之外,最適合給小孩捉迷藏,小時候在奶奶家,只要翻開衣服躲進去,貼著木壁摒住呼吸,除了爸,沒人找得到我。現在的我早就過了玩捉迷藏的年紀,不過,即使爸不用找就看得見我,我也不知該怎麼對他笑了。
這是所狹仄的暫棲之處,曾經佔滿一幢透天厝的記憶全被壓縮進來了,還有許多仍安好地冬眠在未曾拆封的紙箱中。年都過了好一陣子,氣溫卻絲毫沒有回升的跡象。依著紅膠帶的標記,我翻找出裝有冬天衣物的紙箱,抽出一條毛呢大圍巾將自己層層包裹,捧著一杯熱茶,回到冷涼的沙發。我望著沐浴在午後陽光下的客廳,屋子雖然小,窗戶卻如此慷慨,陽光將陳舊的家俱鍍上一層薄透的淡金,讓它們不再黃得難堪。
未來半年都要在這裡過了。窗外傳來敲打與鋸木的音噪。剛才進門前,我瞥見好幾個工人忙碌地穿梭在斷牆破磚之間,國破山河在,原先的家已成廢墟殘壁。昨晚母親在電話裡說,雖然牆壁已經打掉了,但進度還是不夠快,她希望籌劃已久的嶄新裝潢能立即動工──雖然修補一樁崩壞婚姻的機會很渺茫,但是,倘若家屋能成為一幢更宜棲息的住所,至少,至少能稍稍撫慰她殘破的信心吧。更改水管動線後,牆壁便不會再生出灰色癌斑,毛髮與灰塵也無法藏匿在新鋪的木板縫裡,洗碗槽裝上熱水開關,家人就不必再為冬日洗碗煎熬,母親手指紅腫脫屑的老毛病也不會復發。
我自然是期待的,畢竟誰不想要鋪有光亮木板的新房間、飄散原木芬芳的大書櫃?淋浴時再也不必忍受忽冰忽燙的水柱、流量孱弱的蓮蓬頭、長年未乾的浴室地板,還能自由選擇磁磚的花樣、粉刷牆壁的顏色……這樣一想,彷彿此間賃居的所有不適皆可忍耐,所有的權宜都可接受了。
果真是這樣嗎?
聽見他關上大門的那一刻,我不敢問自己。
其實都可以不要的。不要嶄新的液晶電視,不要母親獨睡的主臥房,無需週週上高級餐廳,也無需光滑適手的3C產品。生命和家屋一樣,有一種空缺是這些多餘的事物永遠填不滿的。
不過,這世界從來就不問你要不要的。
父親結束旅遊的那天,年初五晚上他打開奶奶家的大門,手上提著好幾個大紙袋,空氣僵凍的客廳裡,我分不清那究竟是給家人的紀念品,還是他來作客的伴手禮。奶奶除了喚他吃飯之外什麼也沒說,媽的臉色是我見過最鐵青的一次,只有弟弟興高采烈拆著包裝紙。正當他忙著將羊羹和仙貝一字排開,浩浩蕩蕩擺滿桌面時,我發現堆在桌腳的數個紙袋上全都印有機場免稅店的字樣,平整無痕的模樣,應是上機前才包裝好的。我們是他於旅行結束前才想起的。
在我逃離客廳的前一秒,爸裝作沒看見沙發一角鬧胃疼的媽,捧著滿手東西走近。「來不及了」,我想。他手中的零錢包和手機吊飾,竟然都是我喜愛的樣式,還有閃耀細緻光澤的高級耳機,他說,價錢比台灣的貴一倍,遞給我和弟弟一人一副。
那時的心裡藏了太多酸澀的問題,當下卻一句都問不出口。「謝謝」表示接受,問「你和誰去」則太多餘,或是我根本不該伸手,只需轉身離開。不過,或許是由於他灰敗疲憊的面容,或許是由於奶奶默默垂下了她稀疏花白的頭,最後我竟然點了點頭。我恨自己只能點頭。
如果當初我沒有點頭,或許他就不會離開了。
母親告訴我,家的外觀不會有多大改變,但內裡肯定煥然一新。數月來我陪她逛街看家俱,比較各家氣密窗,挑選大門樣式。從家飾店離開已經兩小時了,她依然念念不忘那張鄉村風的米白餐桌。在一家即將收店的傢俱館內,她還半開玩笑地指著那座小巧精緻的象牙白雕花梳妝檯告訴我,「想要的話現在就買」,她的心情難得這麼好,「改裝潢可以改運呢」,她自信地說,笑得卻不夠真。
客廳裡不知不覺已經暗了下來,彷彿有人捻熄了陽光的開關。窗外開始飄起晚春的雨,玻璃外面的雨,看久了,一絲絲走進眼睛裡。電鑽聲從未間斷,我彷彿可以就著聲音想像,被灰色腫瘤佔據的醜陋牆壁是如何被一面面敲毀,大塊龜裂的地磚被一片片掀起……我不曉得該如何移除一幢房子的血肉而不傷其筋骨,我只知道,毀壞一個家的過程很快,重建則不一定,畢竟那是整座生命裡,最最困難的事。
一定能逐漸習慣的,習慣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