語言詩意,充滿無可言喻的想像力。首句即挑明所說的不是故事,而是想像。文中父親病重,而兒子迴避任何反應,反倒回憶早年故事裡。兩個故事雖有輕重之別,成套的,彼此互為隱喻。作者的筆法極為超群。──袁琼琼講評。
父親告訴我,他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沒有血的人。蚊子飛過來,將喙探入他薄薄的皮膚,卻喝不到血,餓死了。他的身上,於是落滿蚊子的屍體。
在醫院,他望著我,等著我為他解夢。曾經挺實的面孔已經塌陷,臉上佈滿黑斑。我為他端去醫院分發的晚餐,一根蒸胡蘿蔔,一點燙過的青菜和一碗米糊。
病房靜寂無聲,我對著房間裏安在某處的人工智慧系統說,放一首歌,算作對他的回應。我不是佛洛伊德。
父親的臉上,掠過期待落空的神色,對夢的好奇讓他活過來一會兒,現在,他又重新死去了。
就在那陣工夫,我聽到一支久違的旋律,它從喇叭裏走出來,走到空蕩的病房上方,盤旋、遊蕩,嗡鳴一般,咒語一般,使我緩緩坐下,坐在父親潔白的病床的一角。
它是我的一位老朋友。這麼多年過去了,它依舊保持著喑啞的聲線,旋律掛滿蛛網,歌詞覆蓋著青苔。技術沒能修復它,時間也不能。我聽不清楚它,就像多年以前。它仍是那首讓人難以辨認的歌。
外面升起藍煙,很濃,彷彿燒鍋爐的人在燒一種藍色的炭。沒多久,藍色便彌漫了整個天空。我聽到從父親胃部傳來的絲絲拉拉的哀鳴,他忽然挺直身體,嘴角流出一條細長的涎水。
這首歌令我想起一些往事,一些可笑的,荒唐的,具有欺騙性的,妄自尊大的往事,其中包含我對神的憐憫。
多可笑又不知天高地厚,但我曾憐憫神。憐憫神,像憐憫一個被惡棍欺辱的女孩。
我那時候是怎麼有這種想法的?我忘了。但想想神得到的——大量嘔吐物,和一點可憐的,作為供奉的花,經書黑色的封皮,被貪得無厭的手撫得鋥光瓦亮,人們祈求將一攤攤嘔吐物變做祝福。他們以為雙手摩挲的是阿拉丁神燈。這就是他們為神做的。
而書記員般的神,恐怕沒有人體諒他,或者,有人肯為他流淚?人們試圖代言他,有人曾擔任他的助手,但都不是出於人道,同情心或者善意,而是為了別的,一些你我都知道的,它們跟崇高不挨邊。
我還記起一位朋友,一間狹長的兒科病房。我們曾共處一室。我的朋友穿著病號服,像一匹凍僵的斑馬。
現在的醫院沒有兒科了,內科外科婦產科皮膚科耳鼻喉科骨科心血管科都還有,但是沒有兒科。婦女兒童醫院也許有,我不知道,我不是女人,也沒有孩子。
我的朋友那年剛滿十歲,是個小小單簧管演奏家。他的單簧管裝在一只黑色的棺槨裏,藏在病床下面。
我比他大一歲。我是個騙子。我對他做過幾次把戲,三四樁吧,也許,我記不太清了。不過那時候我不認為那是把戲,我很真誠,相當認真。
那把戲我曾用來耍寶。那一陣子,我喜歡偷聽別人不經意間哼唱的歌,並記錄下來,在某個沉默的時刻,當作秘密,或者遊戲,告訴他們。
啊哈,我知道你在心裏哼唱什麼。我這樣對他們說。
沒有人相信。他們早忘了另一個自己會洩密。他們不明白,潛意識是秘密的情報員,是自我的叛徒,也不明白人有時會比自己知道的無知。
遊戲一定以我的勝利告終。我將得到彈珠、卡片、麥麗素、遊戲廳幣子,一些驚歎和讚美。我像個無賴一樣不厭其煩地做這件事。我知道遊戲規則——這個遊戲只能玩一次。如果他們再次在心裏哼唱一首歌,我將百分之百失敗。我怎麼會真的知道答案?我說過了,我只是個騙子。猜中後,我便擺出勝利者的姿態,並一概拒絕將遊戲繼續下去的請求,我帶著勝利的果實昂揚地離開。
在那間狹長的兒科病房,我和男孩在一起。他不介意我是個騙子,也許他不知道。我們的病房有個不錯的陽臺。我們通常在那裏玩。有時候沖樓下的過路人吐口水,有時候玩打妖怪的遊戲,或者假裝它是一條幽長的地下隧道,我們在其中冒險。陽臺的牆壁上充滿我們用黃白兩色的粉筆勾畫的塗鴉,還有尿漬。(有時我們會玩點特別的,比如比雞雞的大小,以及它的射程。不過那沒什麼意義)
男孩的奶奶信奉耶穌,每天早上,她都帶著男孩,面朝病房小小的窗戶虔誠地禱告。他們面朝的地方高樓林立,只有一處樓間,顯現著一小段鐵軌。火車在早上和傍晚經過,似乎是為了帶來神的消息。我聽不見奶奶對耶穌說什麼,就像耶穌對她說的她自己也未必知道,因為她耳背的厲害,人還有些呆傻。
她鼓動我跟她信教,她說謊時比我還要真誠。她說信了耶穌,我的病就會好。她給我講耶穌的故事,說耶穌是神的孩子,他來到人間,人間就有了光明。他摸一下癱子,癱子就康復了;摸一下血漏的女人,女人就不漏血了;他又摸了失明的人、被小鬼附身的人、手乾枯的人,他們也都好了。
有一天,她又對我講起耶穌的故事,講到癱子,血漏的女人,失明的人,被鬼附身的人,手乾枯的人。講完後,她問我,孩子,你願意和我一樣,皈依耶穌基督嗎?我看著她,看到她眼底閃爍著渾濁的光,嘴角因激動而微微抽搐。那一刻,我看到的不再是她,也或者,我不再是我自己了。
不。我聽到自己回答。我就是耶穌。
奶奶的瞳孔像石子丟入湖中,她捂著耳朵,見鬼一樣的逃走了。我躺在被窩裏的朋友笑得前仰後合。他說,你好像是個白癡。
我走向他,踏著懸浮的鼓點與沉默的節奏。他被我嚇到,立刻止住笑,問我是否中邪了。我搖搖頭。我問他,每天早上都在祈禱什麼。他將被子蒙上自己的頭,像死人蒙上白布。我將被子掀開。他將被子闔上。我掀開,他又闔上。如此這般。我說我可以幫你。他躲在被子裏不出來,隔了一會兒,他說,他祈禱可以參加後天舉行的校樂隊演出。因為生病,他被撤去了演出的資格,被一個替補樂手取代。
病好以後,這種演出多得是。我說。
他說他的病好不了了,他生的是一種奇怪的病,只要吹單簧管,便會高燒、嘔吐,咳血、扁桃體發炎,脖子腫脹如白堊紀時代穆塔布拉龍的脖子。接著,他會被送進醫院,接受新一輪治療。
那就不要吹了,也不要再參加演出。我說。
他說他要演出。他演出,是為了見到父親。他們很久沒見面了。他父親是音樂家,會世界上所有的樂器,後來他走了,離開家,背著他的樂器,包括那架鋼琴,去了很遠的地方。他父親說,等到他成為校樂隊的成員,在文化宮演出了,他會知道消息,趕來看他。
他在騙你。我說。男孩卻說,他父親是理想主義者,理想主義者從不撒謊。
為了能夠讓男孩上臺演出,我為他想了幾個主意。我先叫他利用護士輪班的時間,去學校找老師,告訴他一切,懇求他,求他恢復他的演出資格。他問我,能行嗎?我對他點點頭。男孩於是信了我的話,決定試試。
第一天,他換下病號服,穿上一件鴨蛋青色的襯衫,溜出醫院。那是個中午,奶奶在窗邊打盹,護士正交接班。管樂隊教師坐在樂器室,擦拭著手裏金燦燦的薩克斯。房間的窗簾半拉著,灰塵在日光的光譜上躍動。他是個頭髮捲曲,不苟言笑的男人,眉毛裏有顆黑豆大小的痣。大大小小的黑匣子,安靜地疊放在架子上,裏面乘著被肢解的長號、圓號、長笛和單簧管的屍體。
你來做什麼,他問男孩,男孩說他要上臺演出。教師冷笑了一聲,什麼也沒說,繼續擦拭手裏的玩具。男孩幾乎要哭出來,他忽然記起教師最討厭學生哭,於是忍住了。他的無名指隱隱作痛,當他吹錯了音節,教師便用從收音機上折下來的天線抽打他的無名指。他默默從房間走出來,回到醫院,告訴我,沒有成功。
我為他出了第二個主意。我叫他去找那位替補他登臺的同學,告訴他一切,懇求他,求他把演出的資格還給他。他問我,能行嗎?我對他點點頭。男孩於是信了我的話,決定試試。
第二天,他換下病號服,穿上那件鴨蛋青色的襯衫,溜出醫院。那是個中午,奶奶在窗邊打盹,護士正交接班。他走後不久,一個新醫生,帶著幾個更年輕的醫生來查房了,他們叫醒了奶奶,跟她交談,複雜的醫學辭彙蹦出來,我一個也沒聽懂,只聽到他說懷疑是什麼癌。什麼癌?喉癌、扁桃體癌、肺癌、氣管癌,也可能是胰腺癌,我忘記了。男孩的奶奶顯然也沒聽懂,因為她總是在大聲問,你說什麼?我一個字也聽不清。醫生嘆了口氣,走了。男孩的奶奶看著醫生的背影,又看看我,問我,他說啥。我搖搖頭,裝作也沒聽懂的樣子。
很久之後,男孩才回來,淺藍色條紋的病號服重新掛在了他身上。他沒有成功,他說那個替補樂手正為明天的演出興奮不已,他太快樂了,他不忍心打擾他的快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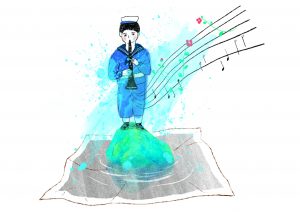
我們站在陽臺上,烈風吹得我們頭髮脹。樓下正對的婦產科的育嬰室,嬰兒在啼哭。男孩輕輕哼起《桑坦露琪亞》,無意識的,彷彿在哄他們睡覺。我說,只要你上臺,你爸就會來,這是你們的約定。不管他們允不允許。
太晚了,他甚至來不及買回來的車票。男孩說。
高樓間露出那截空蕩蕩的鐵軌,神的鐵軌。風鼓動著我的耳膜。一列來自傍晚的火車忽然奔馳而過。
誰能保證那列火車裏沒有男孩的父親?
男孩的身體像一根冰棍兒,被夏天烤化了,他順著牆壁,慢慢,慢慢跌落,最後,他蹲下來,一張皺皺巴巴的紙片從他的褲袋裏掉出來。
我撿起它。是一張照片,年代久遠,一個赤裸上身的男人正坐在一艘木船上微笑,他仰頭,頭髮捲曲,戴蛤蟆墨鏡,下身穿一條牛仔短褲。波光粼粼,湖水蕩漾,船裏放著一把吉他。遠處的太陽很大,隱約看見一座白塔,隱沒在太陽的光輝裏。照片的右下角,一行黑色筆跡記錄著時間:1989.5.31.
「這是你爸?」
「嗯。」
「我見過他。」
「不可能。」
「真的。」
「什麼時候?」
「剛剛。」
「你撒謊,小心我揍你。」
「你打不過我,而且我沒必要撒謊。」
「怎麼證明?」
「你相信特異功能嗎?」
「什麼特異功能?」
「特異功能嘛,就是有的人的眼睛會放電,有的人的身體可以自燃,有的人可以睡在棺材裏,一直不死。」
「不信,你也有特異功能?」
我沒有回答他。隔了一會兒,我說,我們來玩一個遊戲,你在心裏偷偷唱一首歌,我來猜。
男孩看著我,那樣子,像是剛被我施了法。可後來,他還是順從地閉上眼睛,在心裏默默哼唱起來。
毫無疑問,我知道他唱了什麼,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樣。然而奇怪的是,我還聽到一些別的什麼。這從未有過。一開始是雜音,後來是由一些奇怪音符組成的旋律。它就是病房智能系統裏播放的音樂。我很難向你描述它,就像你不能描述一個人臉上意義不明的表情。相當多的時候,語言能做的,只是帶領你想像或者形成通感。所以,我也只能這樣告訴你,那首歌像是從濕漉漉的岩洞發出來的,充滿迴響,每一個音階都像被雨淋過。
《桑坦露琪亞》,我對男孩說,這是我作為騙子所知曉的答案。
男孩被我的回答驚呆了,他的眼中閃爍著所有被我愚弄過的人都閃現過的光。他問我是怎麼做到的。我對他說,人們的心臟就像一個空紙杯,我的耳朵也像一個,一條看不見的線將它們相連,於是我聽到了聲音。我對他說。
他信了,他問我,是否能聽到他的父親,他明天會不會來聽音樂會。我抬起頭,望著那段剛剛跑過火車的鐵軌。
後來發生的一幕,我始終沒搞清楚是真實發生的,還是我想像的。那時,我似乎換上了男孩那件鴨蛋青色的襯衫,邁開腳步,跑起來,躲過辦公室裏的護士,躲過查房的醫生,下樓,走出醫院大門,穿過街道,經過一家賣補習資料的書店,穿過花鳥魚市,穿過百合香氣和鸚鵡的叫聲。我的眼前出現一條窄路,路兩旁是一溜黑黢黢的平房。遠處是長長的鐵軌。就是我之前看到的那條。我翻過一堵紅牆,一下子就跳到了鐵路邊。鐵軌旁鋪滿石子,它們還帶有岩石的鋒利,讓我想起它們在山上的樣子,那時候它們還是一個整體。我走上前,趴在了上面。那並不舒服,石子硌著我的胸脯,耳朵被曬得發燙的鐵路烤的有點疼。但我需要痛苦。我側耳諦聽,我聽到風吹動楊樹、燕子振開翅膀,校園裏的男孩們在踢足球,女人踩著高跟鞋,要到附近的公園約會。然後,我聽到火車駛來的聲音。
我對男孩說,你爸正坐在一列長長的火車上,嘴裏塞滿麵包和香腸。他一定餓了很久。男孩聽後笑了。
我們最終說服醫生,允許他和我在演出那天去了文化宮,在奶奶的陪同下。男孩穿著洗過的,嶄新的校服,拎著裝有單簧管的黑色皮箱。在大門口,他將那張折得皺皺巴巴的照片遞給我,讓我幫他尋找他的父親。
觀看演出的學生和家長陸續走進大廳。我們像兩個追捕逃犯的員警,目光掃過走進大廳的人群。他班裏的同學看到了我們,他們圍上來。後來,身著白色禮服,胸前掛著麥穗樣流蘇的樂團演奏者走過來,他們每個人手裏都拎著黑色的棺槨,眼睛齊齊望向我們,眼神中有點可憐的意思,但沒有一個人同我們講話。樂團男教師在男孩身邊停下,似乎感到疲憊,他問男孩怎麼會來。
他來參加演出。我替男孩回答。男教師將我和我的話看做無物。他拍了拍男孩的肩膀,然後邁開步子,離開了大廳。
人群漸漸寥落,只有三三兩兩遲到的學生和家長,小跑著進入了大廳。奶奶蹲下來,一屁股坐在臺階上,她說她要睡一會,說完,就靠著一旁塗著紅漆的柱子打起盹兒來。我們也坐下來。工人文化宮的院子裏,栽了幾棵高大的梧桐樹,又是毛絮紛飛的季節,空氣裏到處都是毛絮。禮堂裏,幾個嘹亮的聲音開始報幕了。男孩將黑色的琴盒打開,拿出單簧管,按動鍵子,練習著即將表演的曲目,卻沒有聲音發出。奶奶的鼾聲漸漸加重,她開始睡得很沉。
當報幕員報出了晚會最後的節目,我為男孩整理了衣領,他有些遲疑,我說,你爸快來了。他於是拿著單簧管,推開了文化宮的大門。我也從臺階上站起來。我看到光芒萬丈的的舞臺,身著白色演出服的學生,他們正拿著樂器,一排排走上前,逐一落座。我關上門,站在距離舞臺最遠的地方,等待著我背後的大門再一次被打開。
所有演出者落座後,男教師走上前臺,深深鞠躬,隨後背對觀眾,做出指揮的姿勢。男孩就是在那個時候走上舞臺的。他沒有加入那些演奏者的行列,而是站在舞臺左面的一角。那列隊伍裏已沒有他的位置。他深藍色的海軍校服,與那些蒼白的演出服格格不入,像白色巨石旁邊的一朵淺色的浪。他舉起單簧管,也做出準備的姿勢。樂團教師拿著指揮棒的手朝他擺了擺,示意他下去,但是他沒動。台下發出熙熙攘攘的笑聲和倒喝彩聲。一位女教師從後臺走上去,將男孩一把拽了下去。
演奏者快速揮動起指揮棒,《我們的隊伍向太陽》的音樂瞬間響起,高亢、有力,卻機械呆板,像公車上報站名的語音系統。沒過一會,我看到他又一次走上舞臺,站在他剛剛出現的位置演奏起來。女老師半蹲著身子,再一次跑上臺來拉他下去。他在臺上狠狠地掙脫,用力甩著胳膊,如同一隻小獸。台下爆發更大的笑聲。
他沒有拗過女教師的力氣,被拉了下來。台下簾幕的一角,女教師用一根手指,戳著他的額頭、前胸還有胳膊。男孩完全放棄了的樣子,垂著腦袋,慢吞吞地向從禮堂的後方移動。
我衝上前,截住他的去路。還沒到時候,我說。我拉著他重新往舞臺前走,他的手冰涼,像一根冰河裏的枯樹枝,我得想辦法讓它暖起來。我攥緊他的手。我們來到高高的舞臺前。女教師堵住了通往舞臺的入口,她插著腰,臉上寫滿憤惱和厭惡。
上去,我對他說,他像夢醒了,說算了吧。我於是蹲下身。踩著我,我對他說,踩著我上去。女教師向我們走來。我對男孩說,沒時間了。他於是狠狠地踩著我的肩膀,躍上了舞臺,來到臺子的中央,正中央。那個位置,比所有演奏者離觀眾更近,比指揮的男教師離觀眾更近。吹啊,我向他喊,於是他豎起單簧管。
就是那個時候,我聽到了它,又聽到了那種從洞穴發出的聲音,那種細微、濕潤,伴有回聲的音樂。我分辨出來,就是那片曾經出現在男孩心底的雜音,那片掩藏在《桑坦露琪亞》下面的曲調。不同以往的是,它準確,清晰,我完全聽得懂,而且,它是有性別的,它似乎來自於一個陌生男人的哼唱。
他爸爸來了。我回過頭,竭力將舞臺上演奏的聲音驅逐,好讓自己更專心地聆聽。我開始在台下的觀眾裏尋找他父親的身影,我拿著相片,一個一個比照,在昏黃的燈光下,那些黑漆漆的臉彷彿都是一個模樣。我沿著觀眾席的過道走著,時不時將照片遞給那些大人看。
你見過這個人嗎?你見過這個人嗎?
他們有的問你說什麼,有的說太暗看不清,有的只是對我笑。
那聲音越來越清晰了,並且響亮。我流下汗,明明就在附近的,怎麼會找不到呢。我發瘋似的在觀眾席繞來繞去。他們看著我,彷彿我是一隻從馬戲團逃跑的猴子,我想從那些投來的目光中,找到些別的不一樣的目光,男孩父親的目光,但是沒有。
那片來自洞穴的聲音,最後漸漸委頓,消失。等我終於把觀眾席最後一個家長的面目看清楚,舞臺上的音樂也戛然而止了。就在那時,一道光彷彿從我眼前閃過。背對著舞臺的我,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抬起頭。我看到禮堂最後的那扇門,好像被什麼打開了一下,它掀開了一道銀色的線,緊接著,又迅速合攏。沒過多久的工夫,禮堂的燈亮了起來。
後來的事我有點記不大清了。男孩的病回去後就惡化了,他被轉到了更大的醫院,我們完全斷了聯繫。我度過了那段經常生病的日子,此後很久沒有再回醫院,直到今天。
現在,我的父親,帶著對夢的疑惑,進入了另一個夢。可胡蘿蔔、米糊和青菜,還好端端地擺在病床旁的櫃子上。我為他擦去嘴角的涎水,撫摸他冰冷、修長,充滿褶皺的手。那該是一雙音樂家的手。
空氣中的音樂接近尾聲時,藍煙也消散殆盡,奇觀消失了。夕陽染紅了所有。它降落下去的山,失去了細節,只留下黑色的背影。
彷彿是對我的憐憫,在夕陽落山之前,我的耳朵費力地蘇醒了,它聽到了那首歌最後的歌詞。一個微弱的,沙啞的聲音對我們唱著:
Lord , can you hear me, hear me at all?

